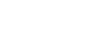【儀表網 行業聚焦點】化的產業改革殊途同歸都是工業和信息的結合。比如:德國的“工業4.0”,我國的“2025中國制造”,日本的“日本再興戰略”,“歐盟2020戰略”等政策。我國在大浪潮里有什么優勢和特點呢?改如何發展呢?
今天,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越發緊密融合,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趨深遠,我們向外的目光需要更遠更深。一方面,金融危機對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仍在持續,世界經濟尚難進入到穩步有序的復蘇進程中,各國宏觀經濟政策仍處于深度調整之中,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面臨極不穩定的外部環境。另一方面,隨著中國成為大貿易國,第二大經濟體,中國對外開放及合作也面臨著新形勢。對外投資額已超過引資額、人民幣化步伐加快,“一路一帶”建設加速推進、中國主導創建亞投行……無不顯示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與思路的優化。
德國提出并推動的“工業4.0”戰略,目前已經成為制造業新一輪浪潮的代名詞。這背后,是德國的再工業化戰略,也是背景下的制造業回歸浪潮。這股浪潮不僅僅將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,也將改變普通人的消費行為,并有可能開啟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。
“‘工業4.0’不光是技術問題,它深入到制造流程控制、標準制定、安全等諸多方面,是著眼于未來的、創新的戰略。這不再是一種‘小修小補’式的政策,而是德國結合自身優勢,尋找下一輪經濟增長點。”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對記者表示,“目前,主要經濟體都在加緊尋找新的增長點。金融危機的爆發意味著上一輪增長周期的結束,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新排位的開始。誰先搶到這一‘棒’,誰就將獲得巨大的紅利,遠遠超越‘便車者’。”
德國:靠比較優勢強身固本
將信息技術與自身強大的制造及科研能力相結合,是德國應對新一輪競爭所做出的重要選擇。對德國來說,推出“工業4.0”戰略,既順應新技術發展潮流,也是未雨綢繆。
從技術上來看,近十幾年來,信息技術進步顯著,無線電通訊、3D打印、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等技術的興起,為工業與信息化融合創造了必要的技術條件。
而更大的動力則來自于德國的危機意識。“德國是個比較務實的民族,并具有憂患意識。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其看到了未來的挑戰。”丁純說。
丁純指出,金融危機使得經濟陷入蕭條。盡管依賴汽車、化工、機械、電子四大支柱產業,德國經濟呈現相對較好態勢,但也感受到了重重壓力。德國以出口與貿易立國,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到德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其在的競爭力。德國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,這場危機使德國意識到,若要加強可持續性增長能力,必須進一步鞏固其在制造業領域的地位。
此外,近年來制造業格局的變化,也使得德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頗感壓力。隨著新市興場的崛起,新興市場在制造業中所占份額逐年增大。羅蘭貝格的統計數據顯示,過去20年,制造業銷售從3.5萬億歐元增加到2011年的6.5萬億歐元。但各國銷售量在總量中的占比發生了巨大變化:西歐傳統制造業強勢國家失去的市場份額超過10%,這部分市場被亞洲、俄羅斯、南美以及非洲等新興地區“搶占”,后者的工業市場份額因此提升至40%。
在對外經貿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所歐洲中心主任史世偉看來,具有強烈危機感的德國感受到以下挑戰:在互聯網信息技術上,面臨美國挑戰。十多年來,從創新的腳步上看,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略遜*,這也成為德國推動“工業4.0”的動力。而在制造業領域上,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。德國擔心,光靠制造業本身,是否能保住其經濟地位。
在上一輪工業革命中,德國處于地位,西門子、博世等都是企業。“‘工業4.0’是人和物、物與物的聯網,是將信息技術與機械制造相連。因此,德國希望依賴制造業與信息產業的結合,找到數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的結合點,保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地位。”史世偉說。
:制造業回歸成潮流
“工業4.0”的橫空出世還具有深刻的背景。”
丁純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,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虛擬經濟膨脹所帶來的風險暴露無疑。各國走出危機,更多依賴于貨幣及財政政策刺激,但這些刺激政策不可持續,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都意識到需要創新,需要有新的性的產業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危機。
實際上,除了德國提出“工業4.0”戰略,在歐洲,提出了“歐盟2020戰略”“智能增長”;在美國,從2009年到2012年,《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》、《制造業促進法案》、《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》和《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》相繼啟動,劍指制造業重振;在日本,“日本再興戰略”成為“安倍經濟學”第三只箭的重要內容。可以說,范圍內,制造業回歸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。
“這輪范圍內的制造業回歸有其必然性,但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‘再工業化’。”丁純表示。
丁純進一步分析說,從來看,制造業回歸趨勢是對金融危機的反應。在危機中,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國家受到了較大沖擊,而德國等制造業比重較大的國家所受沖擊相對較小。通過這場危機,世界各國都意識到過分依賴虛擬經濟是危險的。
“但是,這一輪制造業回歸并不是重復原有的東西,而是有一個飛躍,將市場供需通過網絡技術連接起來,供需更加緊密,產能的控制、技術的提高、成本的優化,都通過網絡黏合在一起,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以及個人消費模式。”丁純說。
值得注意的是,2000年前后的IT技術革命,曾給帶來了一股強勁的增長浪潮。這一輪再工業化浪潮,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會否超越上一輪?
“金融危機爆發后,無論是工業機器人、3D打印還是美國的頁巖氣革命,都曾被寄于厚望,希望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前行的新增長點。但是,現在我們并沒有看到明顯突破。不過,從整個世界經濟的調整來看,這樣的突破一定會實現。”丁純表示,現在主要經濟體都在尋找這樣的“點”,找到了,各國間的差距就拉開。“工業4.0”正是德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,所尋找到的自己所能夠突破的“點”。
中國:如何借鑒德國經驗
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的“中國制造2025”規劃,被稱為中國版“工業4.0”。
“中國制造業雖弱于德國,但互聯網活力并不差。在這一輪浪潮中,中國應大力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,縮短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,實現彎道超車。其實,后來者也有一定的后發優勢。”丁純說。
實際上,無論是“中國制造2025”還是德國“工業4.0”,戰略雖有不同,路徑也不盡相似,但方向都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,其實是殊途同歸。在制造業及研發領域擁有比較優勢的德國,其推動“工業4.0”過程中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。
丁純認為,德國在推動實施“4.0戰略”過程中,國家的頂層設計、對產業標準的重視、所采取的開放式體系結構以及對人才培養的強化,都很值得中國借鑒。值得關注的是,德國強調市場主導,政府更多起到激勵與導向作用,推動市場去做,而不是政府“做了多少事,投了多少錢”。國家政策的強力推動在早期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,但要讓戰略可持續,并終有成果,則不能僅僅依賴國家的政策推動,政策更應順勢而為,應營造一種激勵機制,讓市場之手去主導。
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的胡琨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,真正的創新不能完全依賴外在推動力。在德國這樣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,企業會去主動研發,參與競爭。政府不是以主導者而是以輔助者的角色出現。德國政府提供的是一個方向,提供信息服務,增強政策的透明度,“軟”的支持會更多一些。
史世偉則強調科學界的重要作用。他認為,科學界的獨立自主是德國工業創新體系中的重要因素,這也是對“中國制造2025”的重要啟示。